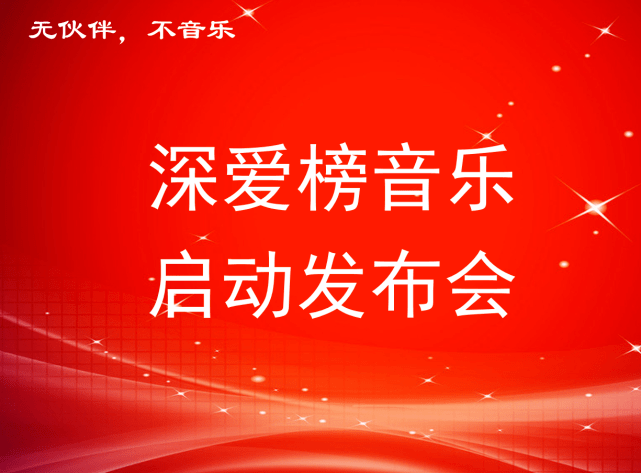|
||
|
||
深圳晚报记者 陈黎
被称为“岭南才子” 的邓康延当过《深圳青年》策划总监、香港《凤凰周刊》主编,然后毫无预兆地“跳进火坑”,辞职去做纪录片。
三年后,当他历尽艰辛、大把烧钱,拍出了远征军主题的《寻找少校》后,这部纪录片为他的公司带来的收入还不足拍摄成本的三分之一。可是当《寻找少校》播出时,很多人当场落泪了。这部片子后来拿了很多大奖,人们不敢相信,这样“不食人间烟火”的片子竟然出自深圳这座现实的城市。
现在,拍完了“少校”、“先生”等一大批撼动人心的纪录片后,邓康延把摄像镜头转过来,对准了一群来自深圳民间的草根,一拍就是两年多。
明天,这部12集系列纪录片《民间》就要来了,在深圳中心书城进行纪录片首播、光碟首发、展览开幕。《民间》到来之前,我们专访了这位民间纪录片制作人,深圳市越众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制片人邓康延。
现在的拍摄 纪录未来的历史
深圳晚报:以前你拍纪录片的人物都是有传奇、有亮点的人,这次为什么会把镜头对准普普通通的民间草根,拍《民间》这个题材?
邓康延:其实好多年了,我一直想拍这个题材。在我所寄生的第二故乡深圳,年轻的移民来了,他们有钱、有闲、有观念,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,也关心这个城市,不断寻找着自己能够为这个城市做的事。在网络发达以后,他们很快地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,聚拢在一起,形成一个个民间组织,为保护海洋、山野救援或者挑战自我等等不同目的共同展开行动……我认为,这种方式开创了人类组织活动、公益活动的一个完全崭新的境界。
我一直觉得,深圳的民间组织,多元、自主、活跃,具有公义良知、现代环保、健康快乐的特质,堪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机的样板。在我看来,他们是以热爱为组织,构筑着人间山水。在深圳这样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城市里,来自民间的草根力量这样蓬勃,我认为,它们也是深圳的一张名片,我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去推他们。
深圳晚报:听说你未来还将继续拍摄更多的民间组织,除了展示来自深圳民间的草根力量,这部系列纪录长片的价值是什么?
邓康延:前段时间,我们在回顾深圳30年历史的时候,去调了很多资料出来。结果发现,这30年中,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场景乏善可陈,几乎就没有,大多数是各种会议和领导讲话。
现在的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。惟有你把这些纪录下来了,许多年以后,人们才能够看到当时的人和环境的真实生态。否则的话,留下来的永远就只有各种会议、领导讲话、形势一片大好、街上的高楼大厦……
这些全都是没有生命力的。惟有人的命运、惟有这个城市的真实轨迹,才是有生命力的,它是纪录片的内核,也是未来我们影视人的财富。
这部《民间》,都是真的人,真的事。我不矫情,不遮掩,直面真实,直击现实,纪实的魅力就在这里。我们拍的纪录片中,有些即使现在播不出来也没关系,因为它们是为未来准备的。纪录片,是面向未来的呈堂供词,它的价值一定在未来。
振臂一呼 全城百公里
深圳晚报:深圳的民间组织数量和种类都很多,为什么选择这12家?
邓康延:在深圳的几十家民间组织中,我们进行反复筛选,选定了这12家。首先,它们都是公益的、阳光的、活跃的,同时它们都有好故事,有的故事很好玩,有的则充满戏剧性冲突。还有的民间组织是深圳所独有的。
深圳晚报:在这些好故事中,让你感到最震撼的是什么?
邓康延:深圳的磨房网连续13年组织的百公里活动。他们每年在网上简单地发布一下活动信息——时间、地点,需要招募义工,马上就有几千义工云集响应,我们去拍百公里活动的时候,发现漫山遍野都是人,有几万人,其中还有海外的华人、港台,上海的、北京的,都赶到深圳来参加活动,非常壮观。
行走百公里,在有些人看来完全是自虐,但是磨房百公里每年都几万人参与,坚持了13年,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。大家都认为,这个现象和这个城市的气场、这个城市所崇尚的那种不拘一格的自我挑战是相呼应的。
如果说人们都是去参加磨房的活动、挑战自己的极限还好理解,可是有些人身体状况根本走不了那么远,不能参加活动,但是他甘愿当义工:守在路口,给参加活动的人端茶送水、指点路标、医护保障、做啦啦队员,看到他们,你能感受到来自民间的那种很阳光的力量。
“拍散”了想上春晚的乐队
深圳晚报:有没有特别感动你的故事?
邓康延:在深圳有一支山野救援队,他们自己掏钱、花着自己的时间,连集训都是每人交200块钱,凑起来进行野外培训。可是他们做什么事呢?一旦山野户外有人被困了、跌下山崖的求助,他们就会紧急出动,赶去救援。
而且他们非常专业。在我们拍的过程中,有一次南澳那边的派出所给他们打电话求助,说有一个自杀者淹死了,家长等着孩子的尸体能弄回来。救援队拿起装备就开车出发了,我们拍摄组也紧跟着一起去了。
当晚风大浪大,岩石上也找不到树,救援队就放了两条绳索,两名队员攀着绳索、开着头灯,吊在山崖上找。一直找到凌晨5点多也没找到,后来在几公里以外的海滩上发现了尸体。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,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。
我们在拍摄过程中,还知道了一件事:他们的前任救援队长在带着救援队户外训练的时候,误食野菜,意外死了,让人感到一种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悲凉。后来他们在救援别人的过程中自己遇到险境,山里淳朴的老乡们又救了他们……这些故事,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对生命的珍惜和人们之间爱的传递。
深圳晚报:都是正能量吗?在拍摄的过程中,有没有感到失落的时候?
邓康延:跟着一支乐队纪录片拍了一年多,结果到最后,拍的乐队散伙了。拍了这么久,和他们已经有了感情,看到这样的结局,确实很失落。
深圳的“原上草”街头乐队,是第一支在中心书城广场上演出的民间乐队,当时政府还没有适应这样的民间乐队,所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,面临着很多冲突和矛盾。
我们跟着他们拍了一年多。最好的时候,他们唱完一天后每个人能分到七八十块钱,他们都很欣喜,觉得今天很有收获,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上春晚。
可是在我们拍了一年多后,他们却要散伙了。其实那时深圳市政府已经开始支持民间乐队,他们的外部条件好了很多,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: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,人人都可以在那个广场上唱,广场变得非常热闹嘈杂,加上他们自身又出现了矛盾,后来一直分分合合,起起伏伏,到最后还是解散了。我们就这样把整个过程真实地拍下来,完全是一个民间乐团发展过程的原生态。
之前我们和央视第9频道联系播出的时候,听说我们拍了一年多,把乐队都快“拍散”了的时候,他们一下就有了兴趣,在他们看来,这种真实的原生态呈现更有价值。
前几天,我们拍到在中心书城广场上,“原上草”只剩下骆老师一个人还在孤独地拉琴,身边也没有什么观众,我们心里也很难受。但是我们的镜头同时也真实地纪录下就在骆老师的旁边,一些新的乐团又出现了,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……
这个真实的镜头让我们领悟到:虽然“原上草”衰败了,但是深圳有这样一片土壤,可以不断生发出很多美好的、健康的东西。